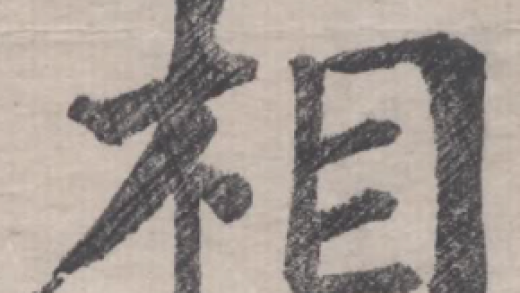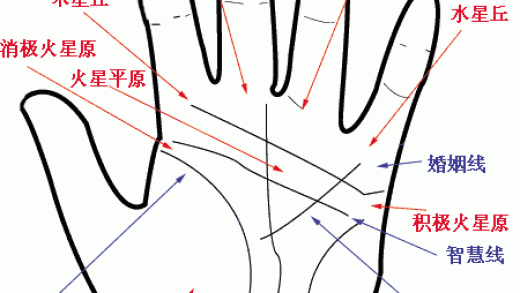不时接到读者的电邮,都说很想研习相学,惟是不知从何入手,请我给他们一点意见。
承蒙读者看得起我,而且那麼热情和渴望,真是愧不敢当。但我没有做过师傅,不知如何教人看相。為了答谢大家,倒不如由我把自己研习看相的过程叙述出来,让有志研习相学的朋友作為借镜。
我喜欢研习相学,时日也算不短了。惟是说来惭愧,一来没有得到甚麼秘笈;二来亦无名师指导,只因对这门学问有兴趣,便默默的自我摸索而已。
曾在本栏说过,当年因為採访审讯战俘,觉得人生恍如一张薄纸,法官大笔一挥,生死仅隔一线。后来在旁观察得多了,便觉得那些能够逃出生天的人,面相上与死囚会有著不同的气色。由於当年不懂相学,只能算是一种直觉而巳。
由於好奇,很想探讨人生际遇的奥秘,便开始研习相学。第一步当然是看相书,因為这是前贤的智慧与心得。我确实看过不少相书,由於我吃的是文字饭,看起书来会比别人快,也容易领悟贯通。有些古籍经典相书是文言,较难解读,郤是难不倒我,因為我的职业就是与文字為伍。以后书看得多了,便去芜存菁,懂得选择何者為精髓,何者是糟粕。
有过一个时期,遇到几位年纪相若而对相学志同道合的朋友,时常切磋讨论。我说出以前看过不少死囚的面相,於是灵感一触,便每个星期选择一天,相约到法庭去看相。
我们坐在旁听席上,儘量靠近犯人栏。每个犯人上庭,我们便目不转睛的替他看相,预测此人将会被判何种刑罚,并把自己的判断记录下来。到了中午休庭时,我们去到茶楼互相比对笔记,命中率最差的人,便要做这顿午饭的东道主。
在那段日子里,我们经常是法庭的常客。这种方法很有用,由於大家都是年少好胜,谁都不愿被别人比下来,於是加紧做功课,也锻鍊了我们的观察力。在这段期间,彼此的功力都大有进步。
说来我很幸运,因為我职业上的方便,常有机会接近名人和富豪,因此看过不少好相。说一句不中听的话,不是每一个看相的人,即使是职业相士,也未必会有看到好相的机会。他们可能由於本身的名气,或者由於相寓所在的地区,前来看相的人,多数是中下层人士,所以他们能够看到的,大多数是穷苦之相。若是不能看到好相,在研习相学来说,总是有所遗憾的。
说到只能看到穷苦之相,使我想起一段往事。那时我在《新报》做编辑,每晚收工,已是深夜两三点。我住在九龙,那时候还没有海底隧道,若从西营盘坐的士去中环,乘搭哗啦哗啦过海,再坐的士入观塘,这笔交通费可就不得了。
上环街市附近有一间茶楼,叫做清华阁,早上三点便开门营业,因為方便附近街市的伙记,饮完早茶便回去开工。我收工后,便和几个也是有家归不得的同事,信步前往清华阁去饮早茶,等到早班电车开动,然后各自回家。
总编辑刘大叔(这是他的本名)收工的时间,比我们还迟些,当然也是清华阁的常客。他平日喜欢谈相,时常都有妙论。他有一句口头禪:“唔到你唔信相”。
有一次饮早茶时,他又提起“唔到你唔信相”,一个同事跟他抬槓,偏说自己不信相。刘大叔用手一指,说道:“远在天边,近在眼前。如果你有眼,可以自己睇。你看而家所有的座上客,有边个好相?个个都泻晒,所以一早就要出来搵食,或者像我们那样,到现在还未觉的苦命人。如果係阔佬,而家重高床软枕紧觉,点会在呢个时候呢间豆泥茶居饮茶!”
同事们平时亦喜欢谈相,此时举目四顾,觉得刘老总的话,确实很有道理,座上客真是难得有个好相,唔到你唔服。
至於看到好相,我的机会真是很多。举些例子来说,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来香港访问,在机场贵宾室开记者招待会。那时香港机场的设备十分简陋,贵宾室内人多挤不下,我坐在李光耀的面前,中间只隔开一张桌子。他有时说英语,有时说普通话。在他说英语时,我听不懂,便乘机看他的面相。
我曾经在中环娱乐戏院(现在的娱乐行)底层的星马协会,单独访问马来西亚总理东姑鸭都拉曼。因為他说的是英语,有人在旁翻译。在听他说话时,我就乘机看他的面相。李光耀和东姑鸭都拉曼,都是国家的元首,难得那麼接近的面对面,这种贵相又怎能错过?
有一次,国泰电影公司在亚洲影展得奖回来。在机场贵宾室中开记者招待会,又是人多挤不下。我恰巧坐在国泰公司的大老闆,也是新加坡首富陆运涛的面前。行家们忙於访问明星,我郤趁著这个机会,观看陆运涛的面相,想找出这个新加坡首富,面相上究竟有甚麼与眾不同的地方。后来他在台湾因飞机失事丧生,噩耗传来,我极為不安,努力在的从脑海中搜索当日的记忆,究竟他的面相有那一处缺点,会使他英年早逝,而且是死於非命。
以前的上流社会,无人不识三叔张玉麟。香港百德新街这个最早也是最大的豪宅区,就是他的家族建造起来的。当时的张家,可以说是富甲一方,但这些财富,都是张家大哥张玉阶赚来的。张玉阶患上喉癌,曾经在全港报章刊登广告,若有人能医好他的病,愿意以一半身家相赠,可是没有人能赚得到这份财富。
张玉阶去世后,张家没有分家,由於二哥早逝,便由三叔张玉麟挑起大樑。据说张玉阶曾有遗言,嘱咐后人多做善事,因此三叔的身上,保良局、东华三院总理这类的衔头一大堆。当时的慈善社团,若想筹募善款,第一个要去找的便是三叔。
由刘、关、张、赵四姓组成的「国际龙岗亲义总会」,六十週年盛会在香港举行,不少宗亲从全球各地来参加。张玉麟当时是总会主席,他想做一件别开生面的事,邀约全港红伶合演一齣粤剧「桃园结义」,因為这是四姓祖先光辉的故事。又请来导演黄鹤声,在现场把全剧拍成电影纪录片,分赠给全球各地的龙岗会所。
这次盛大的演出,网罗了全香港的大佬倌,有新马师曾、梁醒波、靚次伯、陈锦棠、麦炳荣、邓碧云、凤凰女、陈好逑等。所有演出费用,佬倌酬劳和拍片费用,全都由三叔自掏腰包,出手非常阔绰。
有一天,三叔请我去他的豪华游艇「金枝玉叶」吃晚饭。最初,我以為他还请了别人,我不过是叨陪末座。上船后,才知道贵宾只是我一个。看到旁边有八位侍应殷勤招待,不禁受宠若惊。吃饭时,他提出要请我在这次演出中,帮忙做全港报纸的宣传工作。由於他盛意拳拳,而且我也是宗亲,当然即时允诺。三叔笑著说:「因為这是义务工作,请你吃这餐饭,就算是给你的酬劳了。」
虽然我是义工,但在工作上也会有一些开支。例如当时香港报纸的娱乐版编辑,习惯了收受所谓「稿费」;开记者招待会,要发给车马费;也要和行家饮饮食食,请他们多写两笔,多拍几张照片。这些费用,我预早便向三叔说明了。他在报界有不少朋友,对实际情况亦很熟悉,他给我的答覆是:「实报实销」。
三叔习惯於每日两点茶市过后,在永吉街陆羽茶楼地下喝午茶,因為他的公司只相隔隔几间铺位。在这段日子里,我隔两三天便去一次陆羽茶楼,向三叔报告工作进程,把剪报拿给他看,也报销一些费用。他的作风十分爽快,从来不看单据,问了数目,便从西装袋里拿出一大叠当时称為「大牛」的五百元钞票,颼颼颼的便数出来。
和三叔张玉麟接触得多了,心里有著一个很大的疑问。因為三叔的家世,在香港已是家传户晓。大家都知道,他的财富不是自己赚来的,甚至可以说是不劳而穫。由於兄长遗言要多做善事,他可以大笔的花钱,博得善长仁翁的美誉。但在相貌上,说句不很恭敬的话,他长得并不轩昂,走起路来还有点「寒背」,相貌亦不觉得出眾。若是穿著普通衣服,和刘大叔所说的清华阁茶客没有甚麼分别。
他的富贵命究竟在哪里呢?我暗地里观望他的面相,总是没法找得出来,心中不禁纳罕。可是有一天,我偶然看到他的手掌,顿时眼睛一亮。他的掌背没有甚麼异样,但掌心翻过来时,从掌沿起,恍如咸淡水分界,整个掌心郤是一片通红,而且红得很有彩气。
我大胆地问他,可不可以把两隻手掌摊开来,让我看个清楚。三叔嘴角微微笑著,真的把两隻手掌摊在桌上给我看,我猜想他以前曾经看过相,所以知道我想看的是甚麼。我看过他的手掌以后,彼此会心微笑,一切尽在不言中。
这是我有生以来,看过的一对最好的硃砂掌。於是,我恍然大悟,三叔的好命运,全都在他的这对硃砂掌上。